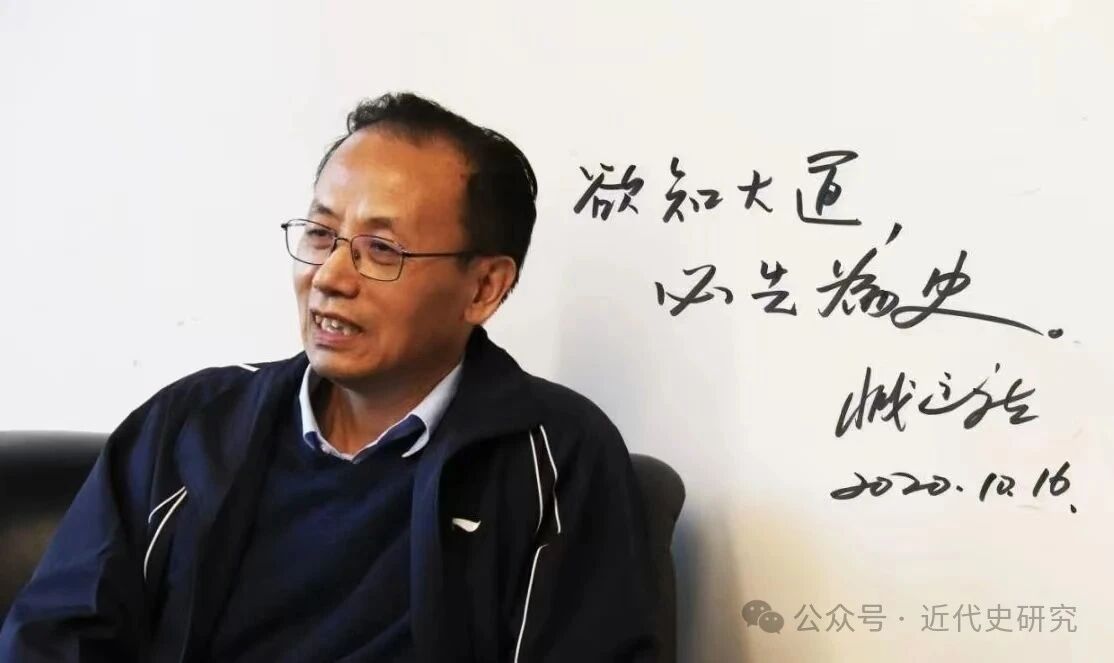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1946年5月4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即将北返复校之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纪念碑,在冯友兰撰写的碑文中,特意书写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 这段作为历史记录的碑文,把近代以来从甲午战争历经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复兴历程,进行了很好的表述,并且指出了抗战胜利作为中华民族复兴枢纽的“旋乾转坤之功”。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近半个世纪中日关系的演变,简述中国人对于日本从师日、反日到抗日、抗战,中华民族从觉醒到复兴的历史进程。
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及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实为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节点。还在马关议和期间,严复就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原强》长文,内称:“呜呼!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战后,梁启超提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酣睡之声,乃渐惊起。”陈独秀也认为:“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
甲午战争以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民族自决意识不断增强,开始了“睡狮”的觉醒过程。随着战后中日关系的“逆转”,先进的中国人继续“睁眼看世界”,并把救亡图强的目标定在“师日”之路。从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从立宪到革命,明治维新以后取得近代化成功的日本,一度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模范。毛泽东曾描述过20世纪初期以前中国人学习西方及日本的缘由:“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但与此同时,走向帝国主义之路的日本,为实现其甲午战前既定的“大陆政策”,从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到发动日俄战争,在侵华之路上狂奔不已、越走越远。“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现实,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对于日本侵略的警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此为“天赐良机”,加紧出兵中国山东,侵占胶州湾与胶济铁路,随即提出旨在实现其“大陆政策”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中之第五号要求则以亡韩手段对待中国,并以“最后通牒”手段,迫使中国政府与之签订不亚于“城下之盟”的“民四条约”。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逼签不平等条约,再次惊醒了中国人长达20余年的“师日”之梦,“五·七”、“五·九”“国耻”的产生,成为中华民族新的觉醒标志。
1915年6月,留学日本的李大钊在《国耻纪念录》上发表署名文章《国民之薪胆》,历数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以来的三次侵华战争史(甲午、甲辰、甲寅),并以此“三甲”纪念,唤起国民勿忘甲寅国耻、致力于复兴民族的卧薪尝胆意识,“吾国对日关系之痛史,宜镌骨铭心纪其深仇大辱者,有三事焉: 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此三甲纪念,实吾民没齿不忘者也。……但知吾国沦降之新地位至于何等,皆日本此次乘世界之变局,强携我国家若民族濒于万劫难复之域,而堕之于九渊之中。吾人历数新仇旧怨之痕影,苟时势尚许我以最后之奋斗,则此三甲纪念中之甲寅,吾人尤愿与之共未来之薪胆生涯者矣。”
日本“二十一条”与丧权辱国的“民四条约”,使得已经形成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再次勃兴,并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达到新高潮。五四运动以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期间再次达到高潮。从“五四”到“五卅”,国民革命时期中国民众反日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到来。
亲历五四运动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的李大钊,在1924年发文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国民党人士也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国民的团结力,更形巩固,学生工人的势力,尤为浩大,自五卅惨案发生,全国民众莫不以内除军阀,外抗列强,为共同的目标,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中国民族复兴的必然,乃因此为全世界各民族所公认。”
九一八事变曾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国难”。国内最早报道该事变、在华北颇有影响的天津《大公报》,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由胡政之、张季鸾召开编辑会议,宣布“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并于10月7日发表《明耻教战》的社评。为此,该报选派记者王芸生往返平津搜集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资料,经过编辑后,自1932年1月起,在第三版正式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特辑,并指出:“从同治十年中日始订条约,到民国廿年九一八新日祸,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连载多日以后,大公报社在4月底结集出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至1934年出版至第7卷。该书出版后,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以书评推介,国内一时洛阳纸贵,日本也迅速出版了译本。张季鸾在该书第一卷的序言中,特别指出通过近代中日关系“明耻”之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关系:“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愿全国各界,人各一编,常加浏览,以耻以奋。自此紧张工作,寸阴勿废,则中国大兴,可以立待。事急矣!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之也。”王芸生也在出版的著作中加入了《古代中日关系之追溯》章,再次明确其写作宗旨:“此书之作,首在明耻。盖发愤图强,明耻为先,而明耻不可不知历史。此书记载六十年来之中日关系,逐步推演,彼日强而我日弱,读此书者,当不胜兴衰之感!知耻近勇,中华民族之复兴系焉”。“今日日本所加于我之横逆,足以唤醒中华民族!天助自助,夫复奚疑?中国复兴之一大机运,亦在于此焉”。
以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著作作为“明耻”之教本,力促民族复兴,天津《大公报》之文功独特而有力。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在继续对日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的同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觉醒意识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文称:“‘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有杂志指出:“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全国上下无日不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口号。”
1935年初开始,日军继续在华北地区制造一系列事端,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迫在眉睫。这年春天,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迅速流传全国、风靡海外。文化界人士曹聚仁曾经描述道:“从敌人进攻沈阳那天起,中国民众心理,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有着中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根据此前发表的“八一宣言”,于12月25日在瓦窑堡会议作出的政治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从七七事变开始,全民族抗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时在北平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日本当时的“中国通”所犯下的历史性错误:“田中义一和土肥原贤二之流说来可悲,他们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得太到家了,但没有研究到最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历史上的一股新兴力量”。而就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的1937年8月15日,在上海的一位日本人,在给近卫首相的建言书中,也发表过与那些“中国通”不同的见解:中国“四亿民众的觉醒与复兴的命运,并不是日本一国的力量所能长期压制的。……现代的日本帝国真正处于兴亡歧路之选择”。
1937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193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国统区主办的《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其发刊词指出,“我们深信,当前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自卫抗战实为我中华民族复兴之必经途径及其起点”。“欲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欲求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实现,其在今天和将来,均舍〔除应〕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别无方法与途径。这是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的关键”。战后日本进步历史学者也指出,“与亡国灭种的危机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现并组织这种民族主义,是民族抗战的主体得以形成、发展,并坚持始终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华民族不是没有光荣的历史,中华民族更不是一个卑屈的民族。但是近百年来,尤其自甲午战争这50年来,中国受这个后起的邻邦的侵略压迫,真是耻辱重重,记不胜记。”“中国人在今天真可以抬头看人了!我们焉得不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之基。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中国共产党于延安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以及经过民主共和国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张闻天同期发表的《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提出:为了实现“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目的,首先要实现“民族独立”,其次要实现“民权自由”,复次要实现“民生幸福”。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包括:(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抗战进入困难时期后,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论述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带给中国人民的主要历史经验:“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三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倡导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中流砥柱。抗战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开辟了无限的光辉前景。 自古多难兴邦。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中国人民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遭受空前未有的蹂躏和苦难,最终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结束,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复兴的历程。“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第一,中华民族巍然独立了;第二,国家近代化的前途畅通了。中国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复兴。”就此而言,抗日战争的胜利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