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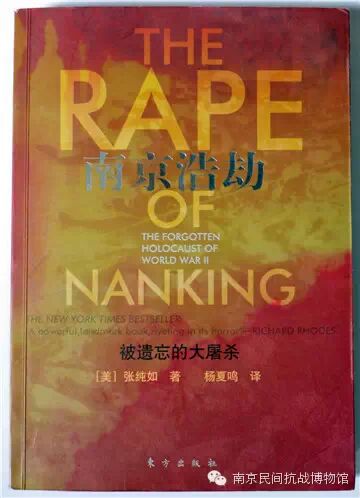
一
2006年12月的一天,作家徐志耕给我打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重新翻译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尽管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手头有另一个重要的项目待完成;尽管在学术界,翻译成果一般不受重视,往往是吃力不讨好,但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原因有三:首先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尽管张纯如的书已经出版十年,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产生了重要和持续的影响,但国内却始终没有一个完整、准确反映原著的译本(包括符合学术规范的注释的翻译),因而,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本书引用的一些史料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全新的,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转引该书史料的并不多见。我在与张盈盈博士通信中曾这样写道:“虽然不能说我是更好的译者,但我目睹了本书的诞生过程,并有相关的学术背景,这是其他译者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我会将做好这一工作当作是对张纯如的一种纪念。”
其次,张纯如去世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举行了一个小型悼念仪式,邀请我参加,但那天我正好有课,未能前往;另外,虽然我在1999年初,发表过一篇有关张纯如在南京的回忆文章,张纯如去世后,新华社记者裴文彬,根据我的那篇回忆文章写的长篇报道也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2月07日 第三版),但我自己在张纯如去世后并没有再写任何纪念文章。现在由我来重新翻译这本书多少也是弥补了这一遗憾。另外,张纯如在南京时,曾希望由我来翻译这本书,后来书出版后,也有类似的表示,我的同学王卫星曾专门与江苏一家出版社进行过联系,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果。在本书出版10年后、张纯如去世三年的今天,翻译本书的任务再次落在我身上不能不说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张纯如回国后不久就将她写的第一本书寄给了我,以后还陆续收到她寄来的其他书和资料,1997年《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后,她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她已经将该书寄给我,但我始终没有收到。后来我从她寄给我的书评上了解到本书在美国颇受好评,再后来从《参考消息》上了解到该书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但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中国方面的一些非议,如:张纯如在书中将日军攻占南京与太平天国起义军攻陷南京进行类比以及另一个更严重的政治问题等(现在看来完全是子虚乌有)。更有甚者,一位我不很熟悉的老兄打电话给我,向我索要张纯如在美国的地址,并说该书有数百个错误,要找她商榷。当时我是将信将疑,因为张纯如在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相当严谨,当时她带来的照片全部有编号,她在给我们看过后立刻按照编号归档。于是我推测可能本书的题材类似中国的“报告文学”,因而阅读该书的热情也大为降低。接着又听圈内人士说,中译本就连高兴祖、孙宅巍、徐志耕这样知名学者的姓名都译错了,于是我对那位老兄所谓的“错误”有了新认识,但从此对该书的中译本也兴趣全无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曾专门发电子邮件告诉她时至今日我还没有读过她的大作,但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也没有收到她寄来的书。大约半年后,收到她的回信,得知她此之前在美国各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不久还要去加拿大演讲。又过了很久,收到她寄来的她与日本驻美国大使在美国公共电视台辩论的文字纪录。我当时的印象是张纯如确实很忙,而且知名度很高。在以后的通信中,我再也没有提过这本书。
翻译这本书不仅使我有机会了解本书的基本内容、结构以及资料来源,进而能够对这本书做出自己的评价,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张纯如南京之行的许多细节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二
为写一本书,只身千里迢迢来到南京采访大屠杀幸存者,并实地感受南京的山水、历史和人文,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了张纯如作为作家的一个基本治学精神和态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我才认识她的。
张纯如来南京前,吴天威教授曾写信给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孙宅巍研究员,请他为张纯如提供帮助,并替她在南京找一名英文翻译。我的同学王卫星与孙宅巍是同事,由于了解我的底细,于是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段时间里为“一位美国作家”当翻译。当时我在江苏省青干院工作,工作压力不大,加上快要放暑假了,也就爽快地同意了(现在我经常在想,如果当年我们学校就实行目前各高校普遍实行的“科研”考核机制,很难想象我会同意花20多天的时间为一位素昧平生的人当翻译)。
7月23日下午,孙宅巍、王卫星和我如约来到张纯如下榻的南京大学西苑宾馆,当时第一印象是没有想到这位“美国作家”这么年轻,简直就是一名大学生。张纯如一口清脆流利的英语常使我联想到口若悬河的美国电视主持人。交谈了解到,当她在霍普金斯大学念研究生时,我也正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学习。她沟通能力很好,也很有亲和力,当她得知我本来可能有机会去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一年时,她立刻表示,要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她当年就会在学校的食堂认识我。由于是校友的缘故,我们之间多了一份亲近感。张纯如的中文尚可,基本能听懂我们的话,但复杂思想需要英文表达。她简述了此次来宁的目的,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是要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二是要实地去看当年的屠杀地点和当年外国人居住过的房屋;三是要收集并翻译中文档案资料。
由于段月萍副馆长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筹建人之一,对幸存者的住址比较了解,孙宅巍随即与段月萍进行联系,段月萍欣然同意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作为翻译,所有活动我都要参加,因而没有时间去收集资料,于是王卫星就承担了这一工作。
7月25日,孙宅巍、段月萍和我陪同张纯如前往当年的屠杀现场,首先去的是挹江门附近绣球公园内的纪念碑,接着是中山码头,然后是煤炭港,再下面是草鞋峡,然后是燕子矶,然后是东郊丛葬地,最后是中华门外的普德寺。每到一地,张纯如都用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的碑文,周围的环境。并常常独自一人站在纪念碑前,久久地陷入沉思。在燕子矶,她将镜头对准了山下的破旧房屋,然后又拉到远处林立的冒着黑烟的烟囱,接着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只和遥远、且朦胧的长江对岸,仿佛是再现当年那些试图渡江的中国士兵的逃亡路径及遥不可及、难以到达的希望彼岸。
7月26日,我单独陪她去了鸡鸣寺、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和中华门城堡。在中国最高的城门上,她既拍摄了附近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也将镜头拉向闹市区的高楼大厦。这些内容后来都出现在她的书中:“在南京最南端的城墙上,穿过灰色的锯齿般的城垛,人们可以看到灰蒙蒙的穷人居住区以及殷实人家的红色和蓝色瓦房房顶,然后向北看,是高大和现代的政府建筑区:政府各部和使馆是西式风格的建筑。凝视东北方,人们可以看到在紫金山深色山脉映衬下熠熠生辉的中山陵和点缀在林间的乡村别墅,它们属于南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市民。然后转向西北,人们可以看到江边码头区的生产活动:工厂冒出的烟柱,煤炭码头的污迹,停靠在码头边的汽船和炮艇。京沪线和沪宁线的铁轨穿过城市,并在城北郊区的下关站交汇。沿着地平线,人们可以看到黄褐色江水在南京城墙外浩浩荡荡向北奔流,然后折向东方。”
在接下来的4天中,在段月萍的陪同下,张纯如先后采访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候占清、李秀英、刘芳华、刘永兴以及侯占清之子。唐顺山是张纯如采访的第一位幸存者,也是惟一一位到张的住处接受采访的。由于是第一次,所以采访的程序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
张纯如首先要唐顺山声明允许她在书中使用采访谈话内容。然后要他简述个人自传(我把它通俗的翻译成叫什么名、多大年龄、住在那里……),接着请他讲述个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在此期间,张纯如拍摄,我作笔记。
唐顺山一口气讲了40多分钟。当时唐顺山已经84岁,但口齿清楚,对过去的回忆还算清楚,尽管有时缺乏逻辑性,明显地存在某种记忆错位,但他腿上和背上的刀疤却是不言自明的证据。唐讲完后,我也坐到镜头前,根据笔记将唐的讲述翻译成英文,在此过程中,张纯如提出各种问题。我的翻译加上张纯如的问题却花了近两个小时。这是采访幸存者花费时间最多的一次。
也许是唐顺山当时的经历最具有悲喜剧的色彩,张纯如在书的第四章将唐顺山的经历作为重点进行了讲述。在翻译时,由于时间久远,我对某些情节的准确性心存疑虑,但在翻译完书稿后,为写翻译后记,我重新看了采访录像,所有的怀疑和不安顿时烟消云散――张纯如非常准确、完整地引述了我当时翻译的采访内容,没有任何曲解或是添枝加叶。
张纯如采访的第二个幸存者是夏淑琴。当时夏淑琴在美龄宫做临时工,我们是在那里找到她的。采访就在露天的树荫下进行,当时天气炎热,蝉的鸣叫声非常响,以致录像中夏淑琴的声音显得很低。夏淑琴讲述了当时年仅8岁的她挨了三刀,一家除她和一位四岁的妹妹外全部被杀,母亲和两个姐姐被日本士兵强奸的悲惨经过。夏淑琴还给张纯如看了她身上的三处刀疤,令人震撼。采访中夏淑琴不时地用手帕擦着眼睛,据夏淑琴说,由于当时流泪太多,落下了眼疾。这一次我们也进行了改进,不再逐字翻译,而是由我翻译一个摘要,然后张纯如提问题。她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这一可怕事件对夏淑琴及其4岁的妹妹后来生活的影响以及夏淑琴现在对日本的看法。接着夏淑琴带我们去了当时她一家被杀的旧址――新开路5号(现在叫马道街)。这一地址和夏淑琴一家的遭遇多次出现在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的日记、书信中。那是一座典型的城南大杂院,一个堂屋是公共空间,同时也是过道,堂屋两边门通向单个家庭,然后是天井,接下又是堂屋,如同迷宫,破旧不堪。在天井里,夏淑琴指这一扇雕花窗户说这还是当年的窗户。一想到这扇窗户目睹了当年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不由地感慨万千。
在张纯如采访的所有幸存者中,李秀英最有个性。一开始她对我们很是冷淡,但在我用南京话与她聊了一会家常,并介绍张纯如此行的目的后,她又对我们非常友好,整个采访过程心绪都很好。她时而坐着说,时而站起来演示当时她与日本士兵搏斗的细节。显然,这给张纯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书中她这样写道:“时至今日,即60年后,(她)仍充满活力,生动地描述并演示了其当时的经历。”张纯如在书中接着写道:
“不久她就听到三名日本士兵下楼的沉重脚步声。其中两名日本人将一些妇女抓走,这些妇女尖叫着,被从房间拖出。留下的那名士兵一直盯着她看,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小床上。有人告诉他李秀英病了,他的回应是连踢带打,将其他所有的人从房间赶到外面的走廊上。
这名日本士兵一面慢慢地来回踱步,一边估量着她。突然,在他还没弄清发生什么之前,李秀英先发制人,她从床上跳下,并从他的皮带上拔出他的刺刀,然后背靠在墙上。‘他吓坏了’,李秀英回忆道:“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妇女也会反击。”他抓住李秀英拿着刺刀的那只手的手腕,但李秀英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领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咬他的手。虽然这名士兵是全副武装,而李秀英只穿着行动不方便的棉旗袍,她却奋力拼斗着,两人相关抓着对方,并相互对踢,直到该士兵处于下风,并大声呼救。
其他士兵跑了过来,毫无疑问,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场景。他们端起刺刀刺向她,但无法刺中她的要害部位,因为那个日本士兵妨碍了他们。李秀英面前的日本士兵又矮又小,她抓住他的衣领可以将他甩起来,进而将他作为盾牌,阻挡另两个日本人对她的刺杀。后来日本士兵对准她的头部乱砍,她的牙齿被打掉,满嘴都是鲜血,她将血吐向日本人的眼睛。“墙上到处是血,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李秀英回忆:“我心里并不害怕,我气极了。我只想跟他们拼,把他们杀掉。”最后,一名日本士兵将刺刀刺中她的腹部,她眼前一片漆黑,昏了过去。”
说道这里,李秀英撩开她的衣服,展示了她小腹部一个可怕的L形伤疤。张纯如用一个特写镜头拍下了这一伤疤。录像中李秀英补充道:“当时穿着棉衣,还有卫生裤,要是再深一点,肠子和小孩(胎儿)就出来了,我就没命了。”
在后来的提问中,除了有关李秀英后来的生活状况外,张纯如还问“现在美国、韩国等国的受害者正在联合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这些人士是否与你联系过?”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张纯如要了李秀英的地址,并说回去后将有关的情况寄给李秀英。
82岁的潘开明,当时是拉人力车的,对老南京非常熟悉。由于平时戴草帽,头上留下了痕迹,手上也有老茧,结果被日本人当作是“中央军”带到长江边去屠杀,死里逃生。在讲述了这段经历后,张纯如问了一大串与当时南京和普通人的生活有关的问题。
在第三章,张纯如描写了老南京:“到1937年,即南京大屠杀那年,南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旧中国的遗迹在其首都的街道上仍然随处可见:小贩挑着担子,一头装小碗,一头装着茶壶;纺织工在露天工厂弯腰坐在手摇纺织机前;面馆里的店员在手工擀面;锡匠沿街行走时他的锡器发出叮叮声;鞋匠在顾客门前修鞋;小孩手捏着中间是一个方孔的铜钱,迫不及待地看着小贩制作糖果;推着吱吱作响独轮车的男人们,车上高高堆起的芦柴既遮住了车,也藏起了推车人。然而,新鲜事物也随处可见:沥青马路正在逐渐取代泥路和石子路;电灯和霓虹灯取代了忽明忽暗煤气灯、蜡烛和油灯;城市用水从自来水龙头流出,而不再是装在桶里当街叫卖;载着文、武官员和外交官的公共汽车和小轿车按着喇叭穿行于黄包车、运送蔬菜的马车及行人和动物间,这些动物包括了狗、猫、马、猴子、甚至水牛或骆驼。”
这其中很多信息都是来自对潘开明的采访。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状况使张纯如感到震惊。张纯如拍摄录像视角无疑反映了她当时的心境。在去幸存者陈德贵的途中,段月萍已记不清如何走,所以我们的出租车在下关二板桥一带绕了几圈,当时那里情况惨不忍睹:低矮破旧的房屋,狭小脏乱的街道,临时搭建的“房屋”随处可见,张纯如在车内纪录下了这一切。陈德贵的住房面积不足六平米,除了一张床,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当我们到幸存者刘永兴的家时,他的老伴说,他在洗澡,开始我还以为他家有卫生间,后来发现他实际上是站在床边,光着上身在“擦澡”,破旧的脸盆里的一点水几乎变黑。房屋狭小、凌乱、拥挤。屋内潮湿,光线阴暗,床上还用着一顶破旧变黑的帐子。张纯如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切。
潘开明住在棚户中,据他自己说,这是拆迁过渡。当时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翻译的,也不知道张纯如听懂了没有。候占清家的光线非常昏暗,从录像中看,一开始拍摄的内容由于光线不足,画面几乎是黑暗的。李秀英的住房状况最好,是公寓房,但张纯如的摄像机仍记录下了肮脏的墙面和破旧的楼道。
张纯如在书中谈到了她的当时的感受:“我所见到的情况令我震惊和沮丧。他们大多住在黑暗、肮脏的房屋里,屋内潮湿、散发着霉味,到处是贫困的痕迹。我得知,在大屠杀期间,其中一些幸存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以至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即使日本方面给予最低限度的经济补偿也会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哪怕是100美元的战争赔偿用以购买一台空调,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采访回来的路上,她郑重地对我说,等到这本书写完出版后,她将去学法律,将来代表这些人与日本打官司以得到日方的赔偿。她认为由日本人代理他们打官司显然不妥;由于中国政府已放弃了赔偿,大陆的律师在这方面将很难有所作为;西方人也不会全心全意地代理这些人打官司。因此必须由她这样的人站出来,为他们奔走呐喊。
那一刹那间,我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感动和羞愧(实际上,由于经历的太多,我已经多年没有被感动的体验了),就在几天前,一次闲聊中,我们谈论到社会公平的问题,当时张纯如认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个人奋斗,并以她自己的经历为例,改变个人的命运是依靠自己而不是社会的救济。而我则认为人的能力天生就有差异,有些人很难完全依靠自己改变命运,因而社会的某种调节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我还举例说,如果我的周围全是乞丐,即便是山珍海味,我也很难有心情来品尝。我当时还认为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青年,对她的观点多少有些不以为然。现在我突然感到自己不仅仅是只会坐而论道,而且近乎是一种人格分裂。一方面似乎信奉着一种崇高的公平理念;另一方面对身边的具体的个体痛苦又是麻木不仁、视而不见。而张纯如则正好与我们相反。作为一名南京人对发生在自己城市的历史事件不了解,对其幸存者的疾苦不闻不问的确是一种耻辱。实际上,在以后的10多年的时间里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资料翻译和研究上,正是源于那一瞬间的感动。
张纯如在书的结语中这样写道:“本书的初衷是向那些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免他们遭到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进一步的羞辱,并为南京数十万受害者的无名坟墓奉献我写的墓志铭。最终,本书却成为我个人对人类本性阴暗面的探索。”尽管张纯如没有明说,但这种变化无疑是发生在南京。
我们可以从她的采访对象的变化中看到这一改变。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候占清时,他的儿子也在场,谈话中无意了解道,他曾因索赔问题于90年代初被拘留过两天。张纯如立刻安排时间专门采访他,并从他那里了解到武汉还有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是中国索赔运动的第一人。80年代曾来过南京,徒步行走数百里,采访幸存者,准备向日本索赔。后来据说遇到了一些麻烦,现在情况不明。张纯如当即决定结束南京的采访后就去武汉。只是在我多次劝说和分析可能遇到的风险后,在最后一刻,她才打消去武汉的念头。
采访幸存者结束后,我还陪张纯如先后去了原金陵大学旧址(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医院旧址(鼓楼医院)、鼓楼、马吉故居(南京十二中)、挹江门、珞珈路25号、宁海路5号、中山陵、明孝陵等地。
期间有一个小插曲。珞珈路25号原是丹麦人汉森的寓所,最初汉森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但后来迫于本国政府的压力撤离了南京,马吉原来的住所及教会在挹江门外,即今天的南京十二中内,南京吃紧后,马吉、福斯特及中国教民搬到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珞珈路25号和鼓楼四条巷德国人潘亭的住所,并在那里度过南京大屠杀的岁月。张纯如来南京前受马吉之子大卫·马吉的委托拍下这两处房屋的录像。正当张纯如拍摄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退休干部模样),大声质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在这里拍照,并暗示要没收照片。由于没有任何禁止拍摄标志,我本想与他理论,但为了避免给张纯如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和颜悦色告诉他这所房屋的经历以及张纯如为什么要拍摄,并告诉他我也在省级机关工作。他听完后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们,然后离开,时至今日我都能清楚地记住他那张“阶级斗争脸”。
事后张纯如什么也没有说,但这一事件对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她坚持无论如何要将她在南京拍摄的所有录像带复制一份保留在我这里,以防她自己的遭遇不测。一二年后我又陪一位研究者去过那里一次,发现珞珈路25号的门牌已经没有了,农民工正在打扫刚刚装修好的房屋,我们乘机进去看了一下。据说它即将成为某位领导人的官邸。
还有一件现在看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是除了在中山陵我为张纯如拍摄了一段录像外,张纯如在南京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和工作照。
8月份后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录像资料,由于西苑宾馆的房间太小,并缺少必要的设备,我们工作的地点是在与西苑宾馆一墙之隔的南京大学科研楼(我妻子的工作单位,内有中央空调)。我们将录像重新播放,我将幸存者的证言分段翻译成英文,张纯如再将英文证词输入到她的电脑中,在此过程中,有些内容我们常常要反复讨论直到双方都满意为止。然后是翻译王卫星为她收集的一批中文资料中的部分内容,王卫星也天天到科研楼来,我们常常在一道共进午餐。饭菜是由我妻子准备的。
1995年一般家庭还没有空调,我女儿也在科研楼避暑。我女儿从小就喜欢看书,张纯如很喜欢她,为她偷拍了不少看书和“研究”张纯如挂在墙上地图的镜头。张纯如和我们也有不少合影,她回美国后很快就全部邮寄给我。其中一些珍贵的照片,被《江苏统战》一位姓吴的记者借走后给丢失了,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认为可以再向张纯如索要,由于没有紧迫感,所以迟迟没有动笔写信,她的突然去世使我意识到这些照片可能是永远的丢失了。
张纯如也去过我家,还弹了一段钢琴。但她认为根据她自己的成长经历,培养孩子的演讲能力是第一重要的,并建议我们找这方面的家教对她进行专门辅导。在工作之余的闲聊中,她还告诉我其父张绍进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作为美国华人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来过中国,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今年3月,张纯如父母来南京,在交谈中我特地核对了这一说法,确切地说,是想确认我的理解和记忆是否有误(当时是用英语与张纯如交谈的),张绍进博士说确有其事,不仅如此,他还补充说,在接见过程中他突然灵机一动,请邓小平为其签名留念,结果代表团其他成员纷纷效仿,结果接见比规定的时间延长了半个多小时。至今,张纯如父母那还保留着邓小平的亲笔签名。
8月中旬的一天,我送她上出租车去机场,原本打算送她去机场,但当天我突然感冒,担心传染给她,也就没有送。在南京期间,张纯如经常生病,显然,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手竟然成了永别,不能不叹息人生的无常。2003年底我去美国国家档案馆做研究,在此前的联系中,她表示她也可能要去,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12月的一天我们通了一次电话,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告诉我她的下一步写作计划,我告诉她我在档案馆里的收获。开始我们用英文交谈,但后来我的手机出了点问题,听不清楚,就改用中文交谈,我当时的感觉是她的中文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情绪很好,没有任何她将要出事的征兆。
三
张纯如从来没有称自己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将自己的书称为“学术专著”。她称自己为作家,给自己的书的定位是“非小说体的专著”,并且强调:“我最大的期望是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其他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去调查南京幸存者的经历。”
所谓的“非小说专著”,就是没有任何虚构的内容,在翻译全书及核对了大部分注释后,我认为张纯如完全做到了这一点。20多万字的书中,共有584个注释,书中绝大部分史实的陈述及对南京暴行的描写都有注释,说明资料来源。这完全可以与任何学术专著媲美。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篇历史调查报告。张纯如以记者特有的素养,不仅通过档案资料、当事人日记、书信、影像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在事发现场对亲历者的采访,了解事件真相;不仅仅是为了调查事件本身,而是为了“汲取教训,警示后人”。其着眼点是放在人类的未来。
尽管如此,张纯如在很多方面完全是按照学术规范进行写作的。这里仅以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为例。人数问题一直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这里仅从纯学术的视角)。客观原因有二:一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到美国在日本登陆这段时间里日本公开销毁了大量政府和军方文件,一些关键文件缺失。如松井在返回上海后,曾下令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在他被解除华中方面军司令前一直没有收到调查结果,如果此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在日本军方档案的某个地方必然存在着该调查报告,但该调查报告从未被发现。二是由于1946年内战即将爆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没有兴趣和精力进行全面、细致的证据收集、甄别工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京审判认定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为30万以上,但在判决书的附录中,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只有955名。另外,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据也不够严谨,存在漏洞。这在客观上后来的争论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如果当年能够收集到10万遇难者姓名,现在可能完全是另一种局面。
在书中,张纯如旗帜鲜明地认为南京大屠杀人数在26万以上,但同时她也将与其观点不同研究结论一一列出:“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数字约为20万。约翰·拉贝估计的人数只有5万到6万人……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称大屠杀的人数应该是在38000到42000之间。日本还有人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数量只有3000人。”在注释中,她还特地完整地引用了拉贝在给希特勒报告中的有关描述:“根据中国人的报告,总数约为10万的中国平民被杀害,但这一数字似乎被夸大了,我们欧洲人的估计数字为50000-60000之间。”
更加可贵的是在“广田电报”的使用上,更加显示了张纯如实事求是的风范。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东京将下列电报内容转发給华盛顿特区的日本大使馆,美国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译了该电文,在1938年2月1日翻译成英文:
自数日前返回上海以来,我调查了日本军队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告。可靠目击者的口头描述及个人(他们的可信性是毋庸置疑的)的信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日本军队过去及目前的行为方式使人联想到阿提拉(Attila)和他手下的匈奴人,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其中许多是被蓄意和残忍地杀害。
要是一般的人必然会将这段电报当成是论证自己观点的铁证,因为从表面看,日本外务大臣在秘密的外交电报中自己承认有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前几年中国媒体就是这样报道的),但张纯如进一步研究了该电报的来龙去脉,并在注释中明确地说明:“该电报内容最初是由《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 Timperley)所写,但该电文被上海的日本新闻检查官员所扣留(参见“红色机器”,日本外交电报,第1257号)后来他估计的30万死亡人数由日本的外务大臣广田签发給华盛顿。这一电报的意义在于日本政府不仅知道田伯烈提出的30万死亡数字,而且在当时试图查禁这一信息。”张纯如的这一结论客观地反映了那一历史事实。
在书中,她还对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的结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并对“田中奏折”的真伪进行了公允的综述。
什么是学者?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尽管张纯如从未自称自己是历史学家,但她却使一些“历史学家”汗颜。
另外,张纯如还超越了研究专门史的历史学家所固有的局限性,始终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荣誉的污点”,并告诫人们:“除非有人迫使世界记住这一事件,否则这种可怕的对死亡及死亡过程的不敬,这种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倒退现象仅仅会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小插曲,被当作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碍大局的小故障。”如果出现这一情况,联想到“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自相残害的例子不胜枚举”的事实,那么人类必然会再次重复相似的暴行。现在看来这一告诫并非杞人忧天。
在书的结尾,张纯如总结了南京大屠杀的三条教训:一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二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才会使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三是“人们的思想是如此容易地接受种族屠杀,并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消极旁观者”。
虽然不能说这些总结是至理名言,但其思考问题视角及境界却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所不具备和难以达到的。
作为作家的张纯如在属于历史学家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显然也招致一些人的不快。在1998年的一篇书评中,美国加州大学的JOSHUA A. FOGEL 在肯定了本书的几个章节后,称,“在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恐怖(事件)时,本书开始四分五裂。部分的原因是她(张纯如)缺少作为历史学家的训练,部分原因是本书的双重目标——充满激情的争论和不带感情色彩的历史研究。”正因为缺少这种训练,“作者相信幸存者告诉她的一切内容;没有对这些信息进行批判性的过滤。”[3]
面对记录着南京暴行的大量、令人发指的历史文献,我不知道任何有着正常情感反应人能否真的做到“不带感情色彩”;当你看到李秀英腹部巨大伤疤时,当你看到夏淑琴身上的三处伤痕,而这些刀伤是她在年仅岁8时由日本士兵留下的时候;当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向你展示这些“历史痕迹”时,我不知道张纯如如何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批判性的过滤”。如果这种专业训练是为了消除人的感情色彩,那么张纯如的成功很可能是得益于没有接受这种训练。至于本书是否“在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恐怖(事件)时,本书开始四分五裂”,敬请各位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毋庸讳言,本书也存在着一些错误:作者在书中论述了20世纪初中国与日本达成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以及将东京审判检察方的资料混同于法官的判决等。另外,书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够规范的地方,如在注释中,一些日文书籍没有出版社;一些中文引文没有标明页码;一些转引资料没有说明等。
“百密一疏”,这些都无损于本书对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和警醒世人特别是西方主流意识的历史功绩。在造神运动已成为历史的今天,这些错误反倒使她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一个怀有正义感、富有同情心、既关注人类命运,更关注具体小人物命运的华裔美国人。
作者简介:
杨夏鸣,男,1958年9月生,江苏南京人。198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199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教授。
近年在《当代亚太》、《美国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江海学刊》、《学术月刊》、《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主义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光明日报》等发表多篇论文。编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国际检察局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翻译《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8),该书被列入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


